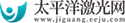怼了单位领导,他们再也没敢在我面前抽过烟
打火机咔吧一声响,我就知道老谢又躲在里间办公室抽烟了。没过多久,丝丝缕缕的烟气顺着门缝爬出来,涌进我的鼻腔。我的内心泛起一阵恶心,在心里咒骂一句该死,拿起手头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室,坐到了公共休息区的沙发上。
我跟老谢共用一间两室的办公室,面积大概25平米,我在靠门的外间,他在靠窗的里间,中间用一道毛玻璃墙隔开,底部的缝隙约有三指宽。他在里面抽烟、煮茶、熏艾草的味道我都闻得一清二楚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老谢是我的直属领导之一,副处级干部,年纪跟我的父亲一般大,姓如其人,早早谢了顶,现在已经是光头了,头皮泛着油亮的光泽。他的光头是他最明显的标志,同一栋楼的同事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,但提起光头就知道是谁。
老谢会热情地跟每个迎面走来的人打招呼,搂着别人的肩膀,大声开一些无聊的玩笑,办公楼的门卫、保洁阿姨和维修师傅都跟他相处得很好。工作时他也想要表现得平易近人一些,会笑着跟人讲话,但好像又觉得这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严,在咧嘴笑的一刹那突然收敛起笑容,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板着的脸。
他看起来是个没有架子的好领导,工作中比较照顾我,经常拿水果给我吃或者开车载我去地铁站。但老谢是个老烟枪,一天几乎要抽一整包烟。他抽烟时会使用一根约莫五厘米长的过滤嘴,用他的话说,可以过滤掉一部分有害物质。这种行为就好比一边吃高热量的垃圾食品,一边又担心自己的体重所以疯狂吃减肥药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我闻不得烟味,上班时经常被呛得头昏脑胀。如果是在夏天,打开门窗通风还可以更快地驱散烟味,但我入职时正春寒料峭,整间办公室密不透风,下班回家后,我还能闻到鼻腔里、衣服上和发丝里残留的烟味。
我偷偷观察了单位其他科室的情况,几乎每个科室都有陈年老烟的味道,黑色皮质沙发、纸质文件,凑近了总能闻到烟味。男领导们常常会在交谈时点上一支烟,烟气袅袅上升,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便不容易关上,就像那些话是从燃烧的烟头里冒出来的。聊久了,烟灰也长了,便随手掸在盛了水的烟灰缸里。烟就要燃尽了,"滋"地一声,烧红的烟头没入水中,这件事情就快聊完了。
每个科室都有女同事,也有不抽烟的男同事,但没有人指出抽烟者的不是,甚至没有人露出撇嘴或皱眉的表情。他们笑眯眯地盯着正在口吐烟圈的男领导们,仿佛那些呛人的烟气根本不存在一样,听到赞同的地方,还要拼命点头,并且附和几句。
他们与这种一团和气的氛围如此相称,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都会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。他们不会主动指出他人的问题,更不会跟同事们闹翻脸,每个人说话做事都礼貌且有分寸,就连稍稍表达不满都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:"今晚又要加班啊!最近天天加班这么累,主任要请大家吃宵夜吧!"
主任笑着回应:"晚点再给你们点宵夜,就是怕你们提前溜掉!"
他们喜欢八卦其他人的家事,话题总是固定的那几个:谈对象、结婚、生孩子、买房、孩子上学、看病;他们也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,以此拉近彼此间的距离。
"小张同志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,再多生两胎啊!"
"这么拼命干什么,不如早点嫁人吧!"
只有我怀揣一个不敢说的秘密,既不会开玩笑,也不想跟大家走得太近,像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。
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,因为公司架构的调整,整个部门几乎被砍掉,我也被迫离职。在广州,没有工作就意味着付不起房租。看到这家单位急招政府雇员,待遇还不错,我便着急忙慌地参加了考试。
这份工作就像一根救命稻草,让我不至于过得捉襟见肘,也因为这点,我不敢贸然指出领导在办公场所抽烟的问题。万一他们给我穿小鞋甚至开除我怎么办?
我有些怀念那家互联网公司,仅仅因为禁烟被列为公司不能触碰的红线,一年下来我没有受到过烟味的困扰,这种对比让我更加反感当下的工作环境。
为了尽可能地少吸二手烟,我只能寻找恰当的时机,在闻到烟味时溜出办公室。我并不打算就此妥协,我不可能在短期内离职,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,我打算尝试一下别的方法。
也许运用诉诸恐惧的办法能让老谢有所收敛呢?我在科普公众号搜索了吸烟危害健康的相关素材,专挑那些含有真实图片的文章转发到小群里,比如长期吸烟者黢黑的肺部和已经产生癌变的气管。
消息没有得到群里两位领导的任何回复,这让我如坐针毡,那一小段聊天记录显得如此扎眼,已经戳破了一团和气的氛围。虽然那些图片看起来触目惊心,但并没有让老谢感到一丝丝恐惧,他依旧抽烟抽得很凶。
有次单位发了一则办公场所禁烟的通知,我看了之后喜出望外,马上转发到小群里。既然诉诸恐惧的办法无法改变他,那么集体制定的规则总该让他有所收敛吧?
结果令我大失所望,跟往常一样,发出的消息犹如石沉大海。老谢依旧我行我素地在办公室抽烟,看文件时来几根,吃完饭来几根,跟同事聊天喝茶时来几根。半年过去,我不知吸了多少二手烟,这让我苦不堪言,上班就像在打仗。
我百思不得其解,明明在其他方面很照顾我的领导,为何偏偏在这件事情上不愿做出改变?在办公场所抽烟本身就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,更何况我已经向他暗示过自己的不满了,他难道意识不到吗?
这些问题我还想不出答案,只能暂时将原因归结为他是个固执的老男人,并为他取了个外号——老东西。
如果我只需要对付老东西一个人,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,但我的另一位直属领导老马也是单位出了名的老烟枪。他是一名正处级干部,也是我和老东西的上级。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,我既是办事员,又是两位领导的助理,承担组内百分之八十的工作。大到撰写各种工作报告,帮两位领导写述职材料,小到登记公车使用,订桶装水,只要两位领导动动嘴,我就要跑断腿。
老马跟老东西的性格截然相反,平日里不苟言笑,也很少主动问起同事的情况。老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的,每次吃完饭,都要先用牙线剔牙,然后再用洗牙器冲牙。虽然他比老东西小了八岁,但对手机和电脑一窍不通,经常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帮他解决电脑使用的问题,因此我私底下也为他取了个外号——老古董。
我们三人开组务会时,便是老东西和老古董相约抽烟的时刻。我观察到他们递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动作:其中一人会先在裤兜里摸索一阵,掏出烟盒和打火机,熟练地用手指夹出两根烟,其中一根递给对方,抬抬下巴示意对方接住,然后毕恭毕敬地为对方点上烟,最后才给自己点烟。
这个动作我在父亲和其他男性长辈们身上也看见过,他们客客气气地分烟、点烟。人多的时候会新开一包烟,挨个递过去,离得太远的会直接扔给对方,每次都扔得很准。
此刻看着两位年长我至少二十岁的男性领导吞云吐雾,我的眼前浮现出男性长辈们的样子,他们的动作如此相似,以至于他们的形象逐渐在我的脑海中重合。
每次看见他们把手伸进裤兜,我的心仿佛一瞬间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攥紧了,我本能地想要逃离,但开会时离开显得很不礼貌,我的教养不允许我这么做。我掩住口鼻,面露嫌弃之色,用笔记本在面前扇风,想通过这些动作告诉他们,烟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了。两位领导瞟了我一眼,又转过头去继续说话,仿佛没有看见我一样。
我受够了他们对我的不尊重,受够了他们的不以为意,也受够了如此畏缩的自己。不满和怨怼在心中积聚,就像火山下滚滚涌动的炙热岩浆,等待喷发的那一刻。
又是一个早会,我刚刚坐下,他们就按照惯例开始分烟了。也不知哪来的勇气,我蹭地一下站起来,语气生硬地说:"我受够你们俩抽烟了,如果你们再在开会的时候抽烟,我就站在门外听你们开会!"
两位领导先是愣了一下,随后收起了已经拿出来的香烟。老古董讪讪地说了一句,不抽了。
我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脏砰砰跳的声音,手心也紧张得出了许多汗,完全无法再集中精神开会。但我又有些得意,不仅因为他们明确知道我对他们抽烟的行为感到不满了,还因为我终于成功反抗了领导权威。这第一次取得的小小胜利,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勇敢。
然而高兴了没多久,我就被老东西叫去谈话了。谈话是体制内的特有现象,当一名干部出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时,领导会找他谈话。我的内心忐忑不安,已经猜到他要对我说什么了。
老东西的臀部深深地陷在沙发里,手指摆弄着一支笔,悠悠地开口说道:"你知道上次开会时你的行为很没有礼貌吗?你这是不尊重领导,你受不了烟味可以好好说,为什么要那样讲话?"
大脑一片空白,我想要反驳,张了张嘴,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就那样站在他面前,沉默地听他讲了十几分钟。他说我太有性格反而不好,要讲究说话做事的方式方法;他告诫我要适应体制内的规则,工作能力是其次,听话才是最重要的……
我就像一个被老师批评的不听话的小学生。我猜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,甚至还有些滑稽。我尽量避免跟老东西产生视线上的交集,直直地盯着窗边的那株滴水观音。那棵盆栽青翠欲滴,不知道它吸二手烟时会不会跟我一样难受。
但植物会净化空气,我的办公室没有这样一大株绿色植物。老东西到底比我惜命,不像我直接用一副娇弱的肺去吸他的中华牌二手烟。
思绪像一尾鱼一样游远了。是啊,我为什么要那样说话?我为什么不学着其他同事的样子,一团和气地开着玩笑把话说出来?如果我不那样说话,就不会站着这里挨老东西的批评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,我的脑海里反复上演那天开会和被老东西批评的情景。
老东西的态度让我确认了一件事: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,他们当然接收到了我释放的那些信号,但他们假装看不见,或者看见了但拒绝承认我的正当诉求,就好像默认我作为下属,理应学会忍受烟味。
大学毕业后,我在家乡的事业单位工作过两年,也遭遇过跟现在的单位差不多的状况。单位的领导班子有五位成员,每位领导都抽烟,其中书记抽得最凶,他可以一根接着一根不停地抽烟,长年累月,牙齿和手指都被烟气熏成了焦黄色,就连他走路时带起的风也残留着明显的烟味。
书记办公室常年弥漫着烟味,扔烟头的痰盂已经被尼古丁和焦油染得发黄发黑。每周一我要做全体例会的会议记录,每周五要去书记办公室做班子会的会议记录,除此之外,还要时不时地被叫去书记办公室听他安排工作。
彼时我吸二手烟的频率和强度都远高于现在,却能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稳坐半天。虽然饱受困扰,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他们不要在我面前吸烟。如今我再次进入体制内工作,却因为吸烟这件事差点跟领导吵起来。
从家乡到广州,工作环境并没有变好,是我变了。我不再像原来那般忍气吞声、担惊受怕,我变勇敢了,也变强硬了,我不想再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
二十岁出头的我跟所有毕业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一样,心里装满了太多的担心和恐惧,担心同事们不好相处,担心领导在工作中给自己使绊子,更害怕激怒了别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更何况我突破重围,经历严格的笔试和面试,顶着120:1的招录比压力,才捧到省直事业单位的这份“铁饭碗”。对于从小到大一直花父母钱的我来说,第一份工作意味着我能自食其力而不必再承受任何愧疚感,为自己的人生消费买单。
我自然变得战战兢兢,生怕出一点差池。我学会了察言观色,学会了理解单位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,只求不要说错话做错事。
在家乡工作时,有天周末,省局下发了一条紧急通知,我直接在工作群@ 了几位领导,提醒他们查看消息。财务科主任马上给我发了条私信:
"不要在群里直接@ 领导,这样显得很不尊重领导,要逐个跟他们打电话说事情。"
虽然我不在财务科工作,那位主任也不是我的直属领导,但我还是撤回了那条消息。等我电话通知完所有领导,做好记录并向每个领导反馈其他领导的意见,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。我感到不解,明明半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,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?
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在体制内工作是如此无奈和无力,这里有严格的科层制,领导权威不可冒犯,领导的好恶和意见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被困在了一张无形的网里,无法伸展自己。
我在那家事业单位工作得越来越不开心,便萌生了离职的想法。我用一年的时间边工作边备考,以初试前三名的成绩考入了广州一所211大学的研究生。我知道读研并不意味着光明的前途,但考研成功这件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——只要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,我就能花时间把它做好。
从家乡那座四线小城市,我又回到了读大学时生活了四年的广州。我对这里的一切依旧感到陌生,复杂且拥挤的交通线路,永远听不真切的粤语,但这里充满了自由的气息,生活里还有许多未知的可能性。
我就像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,从逼仄的笼子里挣脱出来,飞过拥挤的城市和人群,一路飞到了广袤的森林。这里有太多危险,但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。
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心翼翼的姑娘了,我有了工作经验,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,也积攒了一些积蓄。生活于我而言不再是面目狰狞、无法驯服的怪物,它开始变得温顺可亲。我也生出更多的底气去做出跟以往不同的选择。
如今老东西跟那位财务科主任说了一模一样的话,“不尊重领导”。他们没有关注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,仅仅因为我的一些言行就断定我不尊重领导。到底是我不尊重领导,还是我没有做到殷勤地侍奉领导?想到他们面对领导时那种过分殷勤的姿态,我的内心感到一阵鄙夷。
老东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听组长的”,即使他的工作经验更丰富,有更好的工作思路。财务科主任每次跟领导谈事时,都要毕恭毕敬地为领导点上烟,泡好茶,无比热情地对着文件指指点点,生怕领导看不明白。
也许我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,但说话行为本身就已经触到了他们的逆鳞,驳了他们当领导的面子,冒犯了他们的领导权威。我之前也尝试过用各种办法提醒他们了,他们并没有当回事,所以我只能采取强硬的办法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合理诉求。
平时里他们对我的照顾就像老东西突然收敛起的笑容,当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一丁点冒犯时,他们便只剩下板着的一张脸了。
然而,老东西的批评还是让我产生了自我怀疑:在领导抽烟这件事情上,是不是我表现得太过敏感了?
我私底下向同单位的女同事抱怨了领导抽烟的行为,发现她们也会有同样的困扰。
“我们组的领导一般都在楼梯间抽烟,不会在办公室抽。领导人很好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“我们领导也会在办公室抽烟,不过也不是经常抽,我还能忍受。”
“男领导爱抽烟很正常,习惯就好了。”
“我不敢抱怨领导抽烟,这话我说都不敢说。”
我得到了些许安慰,原来不是我太过敏感,只是她们已经默许了这种在男性领导中普遍存在的现象,所以不会跟我一样想着去改变。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,虽然心存不满,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选择自己默默承受。
我有些气馁,为什么在公共场所抽烟的大多是男性,但却要让女性和少数不抽烟的男性付出损害身体健康的代价?为什么我们只能学着忍受而不是争取自己合理合法的健康权益?
虽然挨了批评,但我强硬的态度还是让老东西和老古董有所忌惮,开会或者聊工作时,他们再也没敢在我面前抽过烟。
我总算松了一口气,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阳奉阴违的做派。
老东西确实不会再大张旗鼓地抽烟了,但他会关上玻璃门躲在里间办公室偷偷抽烟,这间办公室的构造决定了,无论他藏得多么深,我总能闻见烟味。
老古董也不在开会的时候抽烟了,但他很精准地拿捏住了我的软肋,知道我不好意思跟不熟的人提要求,在其他同事来我们组谈工作或者我们外出公务时,他还是会毫不迟疑地接过别人递给他的烟。
在场的人当中通常只有我一位女性,对方假装客气地说了一句“抱歉”,便大摇大摆地点上了烟。在这样一个大多数男性领导都抽烟的环境里,我反倒是应该觉得抱歉的那个。
抽烟是一种社交方式,递烟这个动作能迅速拉近跟对方的距离,即使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抽烟还是职级和地位的象征,一般都是职级低的人为职级高的人递烟、点烟。一旦开始抽烟,他们就收获了一种牢固的集体认同,不管什么职业什么背景,大家都变成了同一类人。
姜还是老的辣,作为一名饱经世事的正处级干部,老古董很懂得熟练运用法不责众的心理。
我感到挫败。这场争取自己健康权益的战斗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有了上次被批评的经验,我不打算继续采取强硬的应对方式了,原因很简单,我不想再挨批评。我决定尝试一下老东西口中的“做事情要讲究方式方法”。
曾经被我鄙视的虚与委蛇的体制内做派,到如今我也不得不亲自去实践一番了,也许他们俩吃这一套呢?毕竟他们在这个环境里泡了大半辈子,是体制内的老油条了。
机会很快就来了,今年年初新冠康复后我患上了支气管炎,一点点异味都会让我咳个不停。我去医院拍了胸片,连同病历照片一起发到了群里,告诉他们我患上了支气管炎,闻到烟味就会一直不停地咳嗽,如果造成困扰深感抱歉。考虑到他们俩还没有被感染,我语气诚恳地表达了对他们健康的担忧,建议他们在办公室也要戴好口罩,以免被传染。
说实话,我并不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,如果他们不幸感染新冠病毒,不得不请假在家,那我岂不是至少有一周的时间不用吸二手烟了。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表明我设身处地为领导们考虑,既讲礼貌又态度谦和,“名正言顺”地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吃过药之后,支气管炎两周就好了,这两周时间我几乎没有再闻到过烟味。老东西偷偷抽烟的频率也大大降低了,有时候一整天都没见他抽一根烟。很多时候他选择去楼下抽烟,有好几次我看到他叼着烟嘴在花圃附近徘徊。
总算看到了些许胜利的曙光,我在心里暗暗窃喜。我不敢松懈,继续推进我的计划。
只要发现他们让我吸二手烟,我就会假装咳嗽,咳得两个眼圈红红的,顺势蹲下去捂着我的肺,表情异常痛苦。我在办公桌上堆满了治疗咳嗽的药,等到领导来我办公室时,赶紧假装喝水吃药。
给两位领导“洗脑”的工作也没有停止。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在小群里发消息,内容要么是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文章,要么是我新冠后遗症的症状,比如嗜睡、疲倦、咳嗽、呼吸不畅等等,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保重身体,要多做些利人又利己的事情,比如少抽烟。
老东西似乎觉得有些抱歉,偶尔会回复我一个爱心或者抱拳的表情包,还热心地为我介绍了呼吸哮喘科的老中医。
在这个体制内,我就像个挥舞着剑的战士,朝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宣战,但也许只有我才在意这场战斗,别人或许在笑话我就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呢!
我渐渐明白,自己在意的并不仅仅是抽烟这件事,还有他们作为权力上位者无视我合理正当的需求,连拒吸二手烟这样一件理所应当的小事,都需要我处心积虑去应对。他们越是无视,我就越是在意,非要争出个结果才肯罢休。
这样的努力持续了两个月左右,在一次外出公务时,对方单位的“一把手”给老东西和老古董递烟,老古董摆摆手没有接,语气平和地解释道:
“我们组小黎闻不了烟味,阳康后身体也不大好,我就不抽了。”
“我们去外面抽吧。”老东西竟然也主动为我考虑了。
“一把手”连声说抱歉,收起烟盒,几位领导一起去了室外。
再后来,我几乎不怎么在办公区域闻到烟味了。
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,我觉察到自己内心的能量正在一点点积聚。以往我怯于表达自己的诉求,是因为担心表达之后会被权力上位者剥夺生存资源,比如找借口辞退我。但他们无法剥夺我的生存能力和工作经验,这只是一份暂时的工作而已,我还能找到别的工作,它不应该成为需要我付出健康代价的枷锁。我想现在的我有能力承担最坏的结果。
现在遇到任何有男性领导抽烟的场合,我都敢不卑不亢地说一句“抱歉,我受不了烟味,失陪一下”,然后起身离开。
我和两位领导的关系似乎也发生了转变,以往他们是高高在上的领导,我不敢忤逆他们,但现在他们是两个做了坏事的人,一旦被我撞见,免不了要被我唠叨一句。
当我的内心足够有底气,双手足够有力量,表达就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如果下次我再看到老东西抽烟,我也会学着他开玩笑的语气假装生气地说:
“你怎么又在背着我偷偷抽烟了?你再抽烟我可要提早下班喽。”
更何况,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辞退我了,我已经向单位提了离职,我这只热爱自由的鸟儿要飞往更远处的风景啦!
前几天的散伙饭上,老古董走进包厢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排气扇和空调打开了,老东西笑着问:“今晚最后一次聚餐了,能特批我们抽烟吗?”我欣然应允。这件发生在工作中的小事,虽然以矛盾开始,但好在最后总算是达成了某种圆满。我在想,有时候应得的权利就像挂在枝头的香蕉,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。是的,事情原本不该如此,所以我选择说出来。未来也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