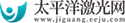乡村叙事的新可能
《鸭镇往事》新书分享会现场。
南都讯 记者黄茜 日前,《鸭镇往事》新书分享会在上海衡山·和集举办。《鸭镇往事》的作者、小说家曹寇,作家、英语文学翻译家俞冰夏,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、文学评论家方岩莅临现场,共话“魔幻与祛魅:曹寇的乡村叙事”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《鸭镇往事》是一部以长三角江边小镇为背景的小说集,鸭镇即为这座薄雾笼罩的小镇之名。由一组关于少年时代的同学、离乡打拼的女青年、迷恋钓鱼的中年人、往返于乡镇和市区之间的打工者的中短篇小说构成。
南京的作家群体
方岩介绍,南京本地的写作氛围特别浓厚,除了在作协体制下生长的一群作家之外,还有很多体制外的作家,他们因为写作的兴趣和秉性上的相通,聚合成一个个写作群体和部落。“比如早年创办‘他们’文学团体的韩东、小海,后来转成导演的朱文,这样一批人,他们各有特别个人化的风格,也在持续创作。严格来讲,曹寇算这个作家群体的第二代,当年跟着韩东、朱文一起,边喝酒边聊天,自己回家闷头写,渐渐有了自己的作品。”
十年前,俞冰夏供职于上海的一家杂志社时,去南京采访过曹寇,还在雨花台的一家云南菜餐厅和曹寇喝过一顿酒。她谈道,南京作家里有“相当个人主义”的一批人,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摆脱了所谓的“家庭叙事”。“我们中国的文学传统是绕不开家庭叙事或社会性的,到现在为止某些地区的文学创作还是按照这个路径在走。但是南京作家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。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进入社会,每个人都在单打独斗,遭遇很多滑稽的事情,甚至用荒诞来消解苦难,好像谈苦难很不体面一样。”
曹寇则坦言,南京作家很多,各个群体的趣味也很不一样。“我现在主要交往比较多的就几个人,韩东和顾前,尤其是顾前,我们两个人家住得很近,经常喝,经常玩儿,经常打牌。”
在方岩的印象里,曹寇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在乎,甚至有点混不吝的作家。“你没有办法跟他一本正经地聊天,他回避特别崇高的词汇或者特别严肃的话题。”
但这样的人有时候猝不及防真情流露,普通读者很容易被他带入情境。“比如小说《父亲》的结尾,本来一直用混不吝的口气叙述一个事情,柔软的地方突然呈现,这时候我感觉曹寇自身有点害羞,我们作为读者也有点猝不及防的感动。”方岩说。
是“鸭镇”也是八卦洲
几年前,曹寇从南京市区搬回老家八卦洲,蛰居乡间,起屋建房,结婚生子。《鸭镇往事》里的“鸭镇”,就是以八卦洲为原型。从行政规划上来讲,这里隶属于南京市,但是它又在南京市的边缘,是农村又非农村,有点像城乡接合部,按照曹寇的说法,类似于上海的崇明岛。
“我居住的乡村已经跟我二十年前离开的乡村完全不一样。”在新书分享会上,曹寇给大家津津有味地分享起他的乡间生活。他谈到,二十年前,农村每家都有茅房,踏入村子时迎面而来的就是各家的旱厕气味。现在,政府号召取缔旱厕,从前的嗅觉记忆一去不返。因为搞新农村建设,乡村里铺柏油路、河道清淤,两岸规划得整整齐齐,像公园一样栽满了奇花异草,非常漂亮。生活也很便捷,有垃圾回收系统,有公交车线路,有宽带有快递,跟市区最大的区别是人口密度小。
“虽然农村这么漂亮,你在村里路上走,都是老人。因为所有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。”曹寇说。如今,四十多岁的曹寇在八卦洲算是最年轻的一个。他看到好多老头钓鱼,自己也去钓,发现钓鱼有极大的乐趣。“我想过这个事,置身荒山野岭,像无人区的感觉,特别好。”
方岩认为,了解了曹寇在八卦洲的日常生活,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进入他的小说。他说:“我们现在对农村的感觉和印象,要不来自于历史的塑造,要不来自于影视剧的虚构,真实的乡村,比如城乡接合部是什么样,城中村是什么样,我们一无所知的。有时候我看一些材料,像城乡接合部、小镇、城中村这样的地带,反而更能代表一种真实的中国。”
俞冰夏谈道,自己家里四五代人,没有一个是农村人,这让她时常感到格格不入。她这一代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好像成了一种没有根基的“新人类”。因为“中国人整体的思维是农耕系统性思维,从管理上的大框架到日常生活上的小框架,都脱离不了这个。”她长期选择做媒体工作,也是为了从“上海市中心很虚妄的叙事”里挣脱出来,触及到有温度的社会现实。
魔幻是更深层次的真实
曹寇的小说大多跟农村有关,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乡土作家。在中国乡土小说的传统里,他最推崇的两位是沈从文和汪曾祺。因为这两位作家的小说都是回忆性、滤镜式的,“他把所有灰暗的东西尽量滤掉,你才看到小尼姑和小姑娘划着小船的美好,你才能看到翠翠和她的狗,翠翠和她爷爷在河边摆渡的样子。”曹寇自己的写作却是另一种类型。方岩认为,虽然八卦洲或鸭镇的确算得上是“农村”,但那里生活着的人们与城市里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“曹寇好就好在这儿,他表面上是在写一群生活在乡村或者小镇的人们的日常,但根子写的是中国人的日常,他不放弃在日常里挖掘一些值得讲述的东西,这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。”
俞冰夏谈道,《鸭镇往事》最让她惊讶的地方在于,“这本书第一眼看去是农村叙事,第二眼看是反农村叙事,明明在写农村里的事情,比如家里儿女有没有出息,房子造没造起来……最后这些东西都分崩离析,每个小说结局传统被打败,尤其是《鸭镇疑云》,这么多有关家庭的东西最后被莫名其妙的人全部瓦解了。”这种写法很无厘头、很后现代。她说,中国乡村叙事的问题在于“苦难”。“我们对苦难好像有上瘾的感觉,不在文艺作品当中表现一点彻头彻尾的苦难,好像这个故事就不是中国人的人生。”然而,曹寇的小说没有用“诉苦”的写法,《鸭镇往事》里也写到了苦难,但“这个苦难首先是有变化的苦难,很多时候是机缘巧合造成的苦难。”
方岩又特别提到曹寇小说中的“魔幻感”,在他看来,这种魔幻代表了更深层次的真实。他特别喜欢《鸭镇往事》的第一篇《龙》:在小说中,一个孩子在雷暴天气看到一条龙从池塘里腾空而起。“你不可以用理性或者所谓的科学世界观去否认这些事情,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溢出日常的东西,这个东西是需要你捕捉的。当你捕捉出来的时候,它就让生活有一种魔幻感,我们未尝不能把这种魔幻感视为一种对平庸生活的调剂。”